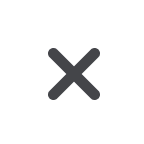不论是在怀孕期间还是接近临产的时候,都是需要患者进行注意的。
其中就有很多的孕妇出现了在临产前有白带增多的情况,这个时候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担心是不是对胎儿有影响,所以就想问下临产前白带增多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下面就让小编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希望通过小编的介绍,孕妈妈们能够提前做好准备。

临产前白带增多可能是患有了宫颈炎,有时甚至是惟一的症状。
宫颈炎、宫颈糜烂治疗前应由医生明确诊断,以排除子宫颈癌前病变和早期宫颈癌。
1、宫颈糜烂时白带一般色黄,质粘如脓涕,多无味;
2、滴虫性阴道炎的白带为稀脓样,临产前白带增多,色黄,有泡沫,或如米泔水样,色灰白,白带味臭;

3、患霉菌性阴道炎时,临产前白带增多,白带色黄或白,多数质地粘稠,有时也可质地稀薄,典型的白带呈豆腐渣样或乳凝块状;
所以孕妇应该警惕临产前白带增多的现象,应该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
1.临产前注意事项:一般在预产期准时生产的只有10分之一,基本上多会在预产期前1周后2周生产,这些均属正常。
新的研究表明,妊娠期最好不要超过41周,因为41周后胎盘开始老化,供血、供氧及营养不足,功能减退。
通常在月经周期正常的情况下,41周后如果还未出现生产症状应想办法行催产或剖宫产术。
2.临产表现:呈有规律的宫缩,有些感到腰酸,有些感到下腹疼,这种痛是能忍受的。
开始疼痛为10分钟一次,2到3小时后为5分钟一次,当疼痛间隔越来越短大致在2分钟左右疼痛一次则说明快要生产了。
临产前宫颈管消失,颈管怀孕时长3公分左右,临产前2周颈管逐渐缩短1.5到1公分,最后拉平消失。
宫口开到10公分大约需10到12小时。
中间以3公分为界线,3公分以前是2小时开一公分,从没开到开共需6小时,到3公分以后是活跃期,每小时大约开1.5公分。
3公分到10公分需要4小时。
一般3公分前痛能忍受,3公分后疼痛加重,到宫口开全就有解大便的感觉,开全以后可以摒气(医生通过肛诊确认子宫开全,宫缩时可以用力摒气)

出现了临产前白带增多的情况,孕妇一定不要着急,因为越是这个时候一定要沉住气。
这样的话才能避免别的问题出现,同时可以尽快去医院进行检查一下。
确认下自己身体的状况。
这样的话也是相当于服了一颗定心丸,同时更好预防疾病的发生。
上海也临海,为什么没人说上海是海滨城市?
上海虽临海却未被普遍称作“海滨城市”,主要因其定位、风貌、文化及历史发展路径与典型海滨城市存在显著差异:定位不同:上海自近代开埠以来,便以连接内地与海洋的枢纽角色崛起,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其“靠海”更多服务于全球供应链和货物吞吐,如上海港作为世界级大港,强调的是集装箱码头的效率与远洋巨轮的繁忙,而非以海洋风光或休闲度假为核心。
相比之下,青岛、厦门等城市以海洋资源为发展本体,海洋直接塑造了城市形象与产业驱动力。
城市风貌侧重不同:上海的标志性景观集中于黄浦江两岸的万国建筑群与陆家嘴天际线,以及市中心的繁华商业区,这些内陆化景观已深深烙印为城市名片。
尽管上海拥有崇明岛、滨海大道等海岸线区域,但它们未成为吸引游客的核心目的地。
黄浦江作为长江支流,其承载的历史文化与现代辉煌,远超海洋景观对城市风貌的塑造作用。
文化和生活方式侧重点不同:上海的“海派文化”融合东西方元素,强调精致、多元与国际化,与直接依赖海洋的粗犷、渔家风情形成对比。
市民日常生活聚焦于市中心的商业、文化与社交活动,去海边休闲更像偶尔的郊游,而非主流生活方式。
海鲜消费与滨海活动虽存在,但未构成城市文化的主流。
历史发展路径不同:上海的崛起源于近代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其发展重心始终围绕贸易、金融与工业化,而非纯粹的海洋资源开发。
这种历史基因使其更像“连接者”与“平台”,而非以海洋为核心内容的“内容提供者”。
综上,上海的“海”更多体现为战略性的地理位置优势与港口功能,而非城市吸引力的核心。
其国际大都市的多元面貌,远超单一“海滨城市”的标签所能涵盖。
轰动清朝的僵尸袭击事件 1872年广西凭祥县灵异事件 民间鬼
1872年的中元节,凭祥人没等到纸钱燃尽,先等来一群“活死人”。村口老榕树下的狗最先察觉,夹着尾巴往山里窜,舌头耷拉老长,像被什么掐住脖子。
第二天,彝族寨子接连抬出三具青脸尸,关节硬得像晒干的芭蕉杆,嘴角还挂着啃了一半的生肉。
消息顺着驮盐的马帮一路炸到南宁,说“诈尸了,会扑人”。
官方奏折写得体面:越南流匪作乱,英吉利人唆使。
可山民不管这套,他们只认眼前——那几具尸体白日晒太阳,夜里真就直挺挺立起来,指甲挠木板的声音刮得人心口发颤。
严树森带团练进山,先放一把火,把整片桉树林烧得噼啪作响,黑烟飘到越南境内,远看像给天边加了一道墨边。
火灭后,他命人把烧焦的土翻个面,撒石灰,再钉木桩写“封”字,动作麻利得像给死人盖棺。
百年后,县医院的老院长在旧仓库里翻到当年尸检记录:死者牙龈收缩、瞳孔针尖大,破伤风+狂犬病毒双阳性。
他把报告拍在桌上,冲学生笑:“哪有什么僵尸,不过是野狗咬了人,人又咬了人,病菌在夏夜疯跑。
”一句话,把祖祖辈辈的午夜噩梦拆成几行病理学术语。
可民俗的坑没那么好填。
直到今天,七月半傍晚,凭祥人仍把白鹅赶在前头回家,鹅掌啪啪踩过青石巷,像给土地打更。
老人说,鹅能看见“那个”,它若突然拧脖子怪叫,当晚就得把菜刀放枕头下。
年轻人一边笑一边照样做,谁也不想拿自己的梦冒险。
2015年,县文化馆把“僵尸传说”报成非遗,展厅里摆了只蜡像“青面尸”,指甲做得又厚又黄,像老茶树板结的根。
游客拍照打卡,买僵尸T恤,没人问那三位彝族老乡到底叫什么。
历史就这样被熨平,变成可以按斤卖的旅游纪念品。
夜里收摊,保洁大妈用拖把蹭过蜡像脚底,嘟囔一句:“真要是僵尸,早跳出去吃人了,还乖乖躺这儿给你赚钱?”说完把灯一关,只剩应急灯绿幽幽地亮,蜡像的脸被映得半明半暗,像随时准备坐起来,又像累了一天只想瘫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