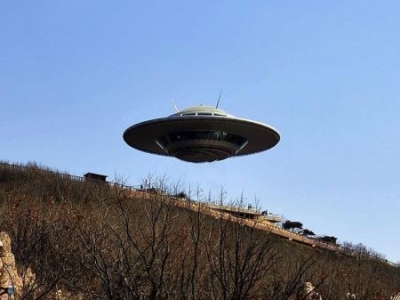胡子的烦恼
本来男人长胡子是件很平常的事情,可是,人类发展到今天,胡须却成了人身体上多余的东西,除极少数特殊人群外,再很少有人愿意留须,一任它在脸上肆意地生长蔓延。

上网搜索,也没有发现胡须对人身体还有什么好处的新说——和胡须一样,一向被看做无用途的眉毛,近来却一路攀升,身价倍增,先是被公认为“脸面的装饰品”,后一跃而为“眼睛的保护神”——大汗淋漓之时,汗水不能从额头飞流直下,遇眉毛而迂回曲折,绕开眼睛。
相比之下,胡子名副其实成为人身体的赘物了。
其实胡子受冷遇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古人对胡须是非常看重的。
据说南唐诗人谢灵运有一把好胡子,当他因遭嫉妒,被人诬告处以极刑之时,监斩官问他临死有什么托付,他说,“死就死了吧,有什么牵挂的呢,只可惜了我这一把好胡子……”你听,在谢灵运心里,胡子比命都要值钱。
清朝重臣曾国藩养胡子也是出了名的,他在给父亲的家书中说:“前父亲教儿养须的方法,儿子只留上唇须,不能用水浸透,黄色的多,黑色的少。
下唇准备等三十六岁开始留……”字里行间透露着对养须的认真和虔诚,是作为一种大文化来传承呵护的,一点不亚于今人对身体主要器官的关注和保护。
古人偏爱胡须,是由当时的审美观决定的。
女脚男须,男人的胡子与女人的小脚同等重要。
据查证,女人裹脚起于唐朝,而男人留须从远古时代就时兴了。
且女人裹脚自唐以后还有时段性,而胡须,作为男性完美的象征、力量的标志、知识与修养的表现等,延续了差不多有人类以来的漫长岁月。
孔子、关羽、沈括、曾国藩、周恩来这些不同时代的历史风云人物,无不挽发垂须,飘然若仙,气度不凡。
现代历史剧中凡老者长者善者,皆蓄髯口,美髯绝伦。
胡须也是权力的象征,拍马溜须,须者,权也。
诗人“吟安一个字,拈断数根须”,由此说开,胡须能引发灵感,是文化的标志。
难怪文人多留须;而武将,书中也多有描绘,虬髯如毡,炸髭似针,再加上一声哇呀呀呀……那就是战斗力。
昔日当阳长坂,张飞手执长矛,大喝一声,吓退曹操百万人马,不能不与他的“胡须倒竖”没有一点关系;男欢女爱,美髯戏金莲,再浪漫不过的爱情了……呜呼!如今人心不古,化繁为简,审美观悄悄发生了变化。
胡须作为男人的荣耀,早已风光不再。
大街上风行长发飘逸,而留须者早已寥若星辰了。
时兴为美。
什么东西不与时俱进,什么就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身体也不例外。
小时候,听到的第一个不雅故事就是《货郎下乡》,说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货郎,挑担来到一个村里,见孩子们围了过来,就把担子一放,让孩子们看玩意。
孩子们不看担子却都仰头看他的脸。
货郎的胡子又白又长,把嘴掩得严严实实。
其中一个大点的孩子指着他的脸喊,快来看啊,他没有嘴。
其他孩子一边围过来一边起哄,像看怪物一样围着他转。
货郎生气了,用手分开长须,把嘴亮出来说,没嘴?这是你娘那腚吗!——凡是第一次听这个故事的人都会哄然大笑,笑的同时眼睛不由地向周围扫来扫去,看在场的有没有络腮胡人。
像这类关于胡子的不雅故事民间有很多,都是指向络腮胡者,你说络腮胡倒霉不倒霉?我第一次因胡须受辱是在我下学后,那时还属于集体。
一次生产队劳动的间隙,社员们围在一起正说着胡子的话题,一个喜欢捉弄人的爷们,走到我跟前摸着我脸颊上还没成熟的汗毛问我,你将来一定不一定一脸络腮胡子?我不假思索随口就答:一定。

顿时在场的社员们哈哈大笑起来。
我哪里知道,这个爷们用此手段不知捉弄过多少络腮胡者,我这个刚刚毕业的高中生面对这种谐音的陷阱也“在劫难逃”。
一定。
一腚。
这一腚络腮胡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这个自取其辱的小桥段,至今想来,我的脸还是红红的。
精神的“折磨”也就罢了,关键是它还“偷人面上花,夺人头上黑”。
这是今人对它最不看好的一点。
挺白净的一个脸面,黑乎乎被它蚕食了一大片,并且随时还有向外扩展之势;挺俊朗的一个小伙,只要与它沾上了边,形象便打了折扣;如果赶上胡须发白,那更是惨不忍睹了。
我有个小女儿,在她七八岁的时候,我领她去赶集,一个我经常光顾他肉案的屠夫见了客气地和我打招呼:这是你“孙女”吗?都这么大了。
我的天,那时我也就四十出头。
当时我还想,我有那么老吗?我心里还骂他:真是猪眼睛。
后来,我多次遇到过这种尴尬的情况。
有一次,我去城外遛弯,与附近小区的一位老者相遇了,攀谈中,我得知他六十八岁,他问我有多大,我说,你猜猜看吧。
他上下端详了我几眼,说了一句:咱俩差不多,你可能比我小一半岁。
我心里一惊。
那年我五十五岁。
这次,我没骂人家猪眼睛。
不是人家看的不准,是自己长得有点太过着急了。
我清楚,这着急的元凶固然与身体的其它方面有关,但关系最大的应该归罪于这满脸的络腮胡子。
社会在进步,人类在发展,胡子有如此德性,哪里还会有人喜欢呢!我有一个老乡,头发自然弯曲,别人给他取外号“毛圈”“三代(羊)”什么的,为此他痛苦不堪。
有一段时间,流行烫发了,让他不再尴尬,他的“自然卷”却成了令人羡慕的美发,自然卷曲,波浪一般,又省却了一大笔开销。
为朋友庆幸的同时,也为自己没有那样的运气而伤心,什么时候,大街上也流行大胡子啊?!胡子没有那样的运气。
不流行的东西就是坏东西。
东北人管胡子叫土匪。
社会上管留小胡子的叫“二㞗”。
人犯王法收拾的首先是头发胡子。
……既然胡子不受欢迎,那就从物质上消灭它吧。
你不让我要脸,我就不叫你露头。
我和胡子之间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用火烧,用线绳绞,用手剔,用镊子拔,用推子剃,用刀片刮,用现代化的剃须工具镟……无所不用其极。
烧之,于吱吱之中产生一股难闻的气味。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绞之剔之拔之,疼痛难忍,据说剔除一根长出三根;推之刮之镟之,治标不治本,胡茬子雨后春笋般没有一天功夫,又破“土”而出,蹬鼻子上脸拉碴一片了。
因拔胡须有过肿头肿脸的教训。
因刮脸不慎,有过鲜血滴滴的惨痛。
因胡子拉碴,有过失恋的痛苦。
一件好好的上衣,衣领破了;一条崭新的枕巾,没几天就烂了一个洞;口罩几天一个;围脖一年一换。
别人出门,只记住“身手钥钱(身份证、手机、钥匙、钱包)”就行,而我出门首先想到的是刮脸刀,一旦忘带将面目全非……这些都是胡茬子惹的祸。
……相信所有络腮胡者都有过我的经历。
烦恼之余,还在算着一笔帐:一片犀牛牌刀片用五天,每片市面价格两元,这样一年算下来就是一百多元的开销,还不说每次刮脸之前之后两次消耗用水、用香皂和毛巾的费用。
现代化的剃须工具价格更昂贵,一个三四百元不等。
质量差些的,用不了几天就报废了。
去理发店省事,但理发店很少有剃须的了,即便有,比理发要多出好几块钱。
头发一月一理,而胡须三天就不敢看了。
花钱是小事,功夫呢?刮一次脸少说也要5分钟,一年浪费在这上边的时间就是三十多个小时。
年复一年,一辈子呢?特别赶上有急事需要出门,而脸面还没有修整,那过程就可想而知了,手忙脚乱,心慌意乱,偏偏这个时候忙中出错,脸又被刮破了………这倒霉的胡子就是这样和你过不去。
什么都有老,唯独胡子没有老。
工人上班还有风工雨工,还有礼拜节假日,而胡须无时无刻不在生长。
人的生活水平越高,它长得越加疯狂。
人到中年有谢顶之人,浓密的头发稀疏了,衰败了,而胡子却依然如故,“一头好脸,一脸好头”,形象打了折扣。
人到老年,胡子还是那么旺盛,虽然苍然了,生命力依然顽强不屈,看不出一点衰败的迹象。
人死了,胡子还长不长呢?没有机会观察,未尝可知 !胡子,可烦可恶。
生之肉长之肉有何办法呢?总不至于和屁股互换植皮吧,那胡须长在屁股上,又将是什么状况呢?!由此我想,人的一生,为了脸面的光彩,为了身体的尊严,也要做一些无实在意义的事情。
作者简介:于世忠,东营河口人。
教师出身,现已退休。
内退后为了排解身边的孤独,一边侍弄菜园子,一边学码文字。
不为名利,只为乐趣。
他把这定性为文化养老。
声明:本网站的主要内容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及东西方的民俗文化,并非严谨的科学研究成果。
仅供娱乐参考,请勿盲目迷信。
本文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如有内容侵犯您的合法权益,请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第一时间安排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