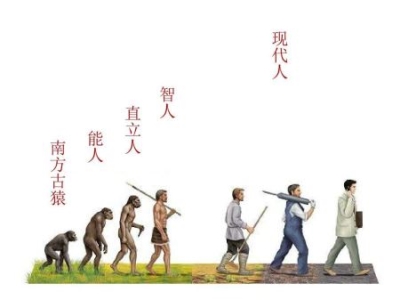假如你要来到这世界上,最好出生七次
”1972年,约翰·伯格基于BBC同名电视系列片写成的《观看之道》出版,而1973年到1974年的上半年,面对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他与瑞士纪实摄影师让·摩尔共同创作了《第七人》,书中文字与图像具有相同的地位,都可以从自身角度解读。

他们希望通过这本书,展现欧洲富裕国家的经济如何逐渐依赖贫困国家劳动力。
作为一本混杂了社会学、经济学、新闻报道、哲学、晦涩诗歌和黑白图像的小册子,书中的数据、背景本应不再有效,书会变得过时。
但联想到今年大热纪录片《美国工厂》、英国货车集装箱后发现的39具尸体、被捕的25岁爱尔兰司机……我们很容易看到,哪些事物改变了,哪些事物依然没有变化。
《美国工厂》@澎湃新闻今天正值约翰·伯格逝世三周年,理想国最近推出约翰·伯格与让·摩尔合作的两本非虚构作品《第七人》、《幸运者:一位乡村医生的故事》,首次引进出版“他们的劳作”三部曲之一《猪的土地》与伯格新近创作小说《到婚礼去》。
从这些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伯格在他所有写作中的开放,就像一只没有快门的镜头。
启程:头等舱、货车、体检,他们用这三种方式穿越边境移民者带着他自己的决心,在家里准备的接下来两三天吃的食物,他的骄傲,他口袋里的照片,他的包裹,他的手提箱。
但是他的迁移就像是别人梦中的一场行动。
作为一个陌生人梦中的人物,他的行为看起来都是自发的,偶尔会出乎意料,不过他做的每一件事——除非他反抗——都取决于做梦者心智的需求。
放弃隐喻。
移民者的意愿中处处渗透着历史必然性,但无论是他还是他遇到的任何人都意识不到这一点。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生活就像是一场别人的梦境。
一个土耳其人说:“在乡下,一年中一半的时间你都在睡觉,因为没有工作可以做,而你又很穷。
”在某个时刻,他穿过了边界。
这不一定是他的国家的地理边界,穿过地理边界是不算数的。
边界仅仅是指他轻易遭到阻拦或是意愿受挫的地方。
当他穿过边界的另一端时,他就成了一个移民工人。
他也许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穿过它。
下面是三种描述穿越边界的方式:一个土耳其农民没有通过官方的体检,他决定以一个游客的身份进入德国。
但在一列拥挤的火车上说自己是一个游客的土耳其人,也许必须通过表明自己带的是什么货币或者支票来向边防警察证明自己的身份。
因此这位农民买了一张去科隆的头等舱车票,自信满满地认为自己坐在头等舱的小客房里、包裹在金钱的气息之中,他就不会被警察盘问了。
他穿过了边界。
直到最近,大多数葡萄牙的移民都是非法的。
无论是穿越西班牙还是法国的边界,都要秘密进行。
里斯本的走私犯会安排这样的越境行动。
他们收取的费用是每人350美元。
但多数付了这笔钱的移民都被骗了。
他们被领入刚刚穿越了西班牙的边界的群山中,然后就被扔在了那里。
这些移民完全迷失了方向,有的人因为饥饿和日晒雨淋而死在那里;有的人能够找到回来的路,350美元打了水漂。
(那时的350美元相当于葡萄牙农民一年的平均收入。
1964年葡萄牙的人均年收入——算入了上流阶级的平均收入——是370美元。
)因此移民们设计了一个保护他们自身利益的系统。
在离开之前他们会为自己拍下照片。
他们将照片撕为两半,一半交给他们的“向导”,另一半留在自己手中。
当他们到达法国之后,会把自己手中的一半照片寄给在葡萄牙的家人,以此证明他们安全地穿过了边界,“向导”拿着另一半照片到他们的家中证明是自己将他们送过边界的,这时家人才会交付那350美元。
移民们会组成一百人左右的队伍集体穿越边界。
大多数时候他们都在夜里上路,藏在货车中,然后步行。
9天之后,他到达了巴黎。
他有一个葡萄牙朋友的地址,但是他完全不认识路。
为了到那里,他必须打一辆出租车。
在允许他打开车门之前,出租车司机要求看看他的钱。
有一个警察就站在附近。
警察和出租车司机一致认为要去圣丹尼的棚户区,乘客必须付双倍的价钱。
他没有问为什么。
他是一个初来乍到的移民,没有钱打出租车,也没有争辩的底气。
他也穿过了边界。
从伊斯坦布尔出发的移民大多去了德国。
他们穿越边界的行动是官方组织的。
他们去了招聘中心。
在那里,他们接受体检,并且经过测试证明他们具备他们所宣称拥有的技能。
那些通过测试的人立即与将雇用他们的德国公司签署合同。
然后他们乘上一列劳工火车,坐上三天。
到达之后,德国公司的代表们会接上他们前往他们的住处和工厂。
他和几百个新来的移民一起脱掉衣服排好队。
他们匆匆一瞥(盯着看就会暴露出他们的惊讶了)用来对他们进行检查的工具和机器。
他们也匆忙地互相打量对方,每个人都试图比较自己与周围人的机会。
对于这样的状况他没有任何准备,这是以前从未经历过的,但这已经是常态了。
在陌生人前赤身裸体的羞辱性的要求,发号施令的官员说出的听不懂的语言,测试的意义,用毡笔写在他们身上的编号,房间死板的几何形状,穿着工作服的女人就像是男人,弥漫着某种未知的液体药物的气味,和他一样的许多人的沉默。
大多数人沉默的外在表现并不代表他们心中镇定或是在做祷告。
如果说这已经成为常态,那是因为重大的事情正毫无例外地在他们每个人身上发生。
合格的人被选出来,不合格的人被剔除。
五分之一的人通不过测试。
那些通过测试的人则会开始一段新生活。
机器正在检查他们身体内有什么看不到的东西。
有的人为了这一次穿过边界的机会等了八年。
一个男人问有没有一台机器会检查出他所害怕的自己脑袋里的一种疾病——令他无法识字的疾病。
体检结束后,还有检验他们是否能够胜任工作的技能测试。
让他们看看你有多强壮,一位朋友如此建议道,回答问题的时候不要着急,然后让他们看看你有多强壮。
一些人坐在那里等待结果。
还有人在来回踱步。
许多人脸上的表情让人想起另一个场景——在产房外等待孩子出生的父亲脸上的表情。
在这里,他等待的是自己的新生活。
他通过了测试,他重生了。

这次的移民现象与此前移民现象之间的区别是,它是暂时性的。
只有少部分的工人被允许永久地留在他们所去的国家。
他们的工作合同通常是一年的,最多也只有两年。
移民工人前往那些劳动力缺乏的地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他获得批准从事某种特定的工作。
除了努力工作以外,他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权利、要求或是现实。
而工作能为他提供报酬和住宿。
如果他不工作就会被送回到家乡。
移民来的不是人,而是机械师、看门人、挖掘者、水泥搅拌工、清洁工、钻工等等。
这是暂时性移民的意义所在。
移民者必须要回到家中才能重新成为一个男人(丈夫、父亲、公民、爱国者)。
他之所以离开家是因为对他而言那里没有未来。
工作:想想它能为你的家庭做些什么,这是唯一的答案人群从几个不同的方向汇聚到工厂的大门。
数以千计的男人和女人,步行的,骑自行车的,开车的。
他们共同的目的地迫使他们靠得更近,直到他们都肩并肩站在一起。
但是,除了一些简单的问候外,他们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彼此,每个人都陷在自己的思绪中,就好像每个人都分别在那天早晨收到了一条消息,迫使他们来到这里。
当他们还在外面没有打卡上班的时候,他们可以选择转身直接离开,他们之间显得如此疏离,以至于他不禁怀疑这些人是不是都像他一样,是从不同国家刚刚来到这里的移民工人。
如果要尝试理解另一个人的经历,就必须先将一个人从自己所处境地看到的世界拆散,然后再按照他所看到的重组起来。
比如说,要理解另一个人做出的选择,那么就必须要想象到也许他并没有其他的选择。
那些衣食无忧的人是无法理解饥困交加的人所做的选择的。
要想理解另一个人的经历,就必须将世界拆散再重组,无论这个过程有多么艰难。
谈论如何进入别人的主观思想是有误导性的。
另一个人的主观思想不单纯是对相同的外部事实构成了不同的内部态度,以他为中心所汇集的事实是不同的。
他被教会如何工作。
当他能做这份工作的时候,他可以在加班的情况下一周挣到40英镑。
他观察别人的动作,然后学着去模仿他们。
如果要用语言讲的话,就必须找到会说他的语言的人。
现代的大规模生产预先假定了参与工作的劳动力大多数是不具备技能的。
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亨利·福特宣称他的工人中百分之七十九的人可以在八天内学会他们的工作,百分之四十三的人可以在一天内就学会。
现在也是如此。
抛开教学不谈,过去两个世纪的历史完全如地狱一般。
很难说是否恰恰在这个时期邪恶力量的观念被摒弃掉了。
在发达的欧洲国家,每个上学的孩子都会学习一些有关此前资本主义历史的知识——无论教科书本身如何掩盖或充满偏见:奴隶贸易、济贫法、童工、工厂环境、1914年到1918年的世界大战。
面对这样的记录,资本主义系统宣称其自身已经进化了,那些过去的不人道行为将不会重演。
一切大众传播中都隐含着这样的断言:我们生活在一个尊重人权的民主系统内,因此我们也在这样的系统内受到教育。
对于这个系统的本质而言,过去发生的暴行都仅仅是偶然的。
他们观察别人的动作,然后学着去模仿他们。
每一个单独的动作也许本身不会太费劲,但是不停地重复这些动作,并且要做到精准无误,从几分钟一直到几小时,动作的累积使人筋疲力尽。
工作的节奏让人根本没有时间去为每一个动作做准备,去调动身体中的力气。
身体在完成动作的过程中已经失去意识了。
提高了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社会福利、议会民主制度、现代技术带来的好处,这些都被用来证明过去出现的不人道行为都是偶然的。
在大都会中心,人们普遍相信这样的说法。
在那里是见不到最赤裸裸的剥削形式的,因为这样的现象发生在第三世界的对峙点。
这里的对峙点既指文化上的,也指地理上的。
一处巴黎近郊的“贫民窟”是属于他们的。
移民睡在属于他们的地下室里。
他们就在那里,但是他们不会被看到。
与此同时,本土的工人被塑造成了消费者,希望后者能够在工作不自由这件事上抚慰前者。
一个在福特工作的英国工人说:“你在这里什么也没做成。
一个机器人就可以做你的工作。
这里的生产线是为傻瓜们准备的。
它不需要任何思考。
他们就是这么告诉你的。
‘我们不会为了你的思考付工钱’,他们说。
每个人都开始意识到他们在做的并不是一件值得做的工作。
他们只是生产线上的一环。
为了挣钱。
没有人愿意去想他们自己有多失败。
当你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齿轮的时候,那种感觉是很糟的。
你只需要想想自己的工资——想想它能为你的妻子和孩子做些什么。
这是唯一的答案。
”他开始观察自己的手臂,就好像驱使它动起来的是它握着的东西而不是他的肩膀。
他思考用抽水泵驱动他的手臂。
移动的零件抓牢他的目光,空气充斥在他的肺里。
他把机器渗出的液体擦掉,那液体看起来就像是一条鱼被从水里抓出来停止挣扎时嘴边流出的液体。
他知道他在做的事情跟他自己拥有的任何技能都没有关系。
他可以用稻草塞满一个鞍座。
他曾经被告知工厂生产洗衣机。
想要理解一种“正常的”、熟悉的整体处境是很困难的。
更确切地说,一个人做出的是一系列习惯性的反应,尽管这是个人的反应,但实际上这些反应是属于整体处境的。
历史、政治理论、社会学能够帮助一个人理解所谓“正常的”仅仅是一种规范而已。
遗憾的是,这些学科却常常被用来做着相反的事情——它们服务于传统的方式是提出问题,而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将规范神圣化为绝对真理。
关于在你身上真正发生了什么,每一个传统都禁止提出某些特定的问题。

“正常的”行为只有在与其完全相反的行为出现时才能完全体现出来,也就是“反常的”“极端的”,或是革命的行为。
当正常的行为被如此剥离了其常态时,一个人对于作为一个异类的正当观念就超越了其自身,而扩展到了他生活所处的整个历史时刻。
然后我才意识到施加在我身上的是什么,我自己做的是什么,并且我才发现我身上有多少东西都是被“正常”否定和压抑的。
要想理解另一个人的经历,一个人要做的不仅仅是拆解并且重组以他为中心的世界。
还必须审视他的处境,以此了解他那一部分源自特定历史时刻的经历。
在正常状态的掩盖之下,即使在他自己知情的情况下,他被施加了什么?这些施加在他身上的事物是新出现的吗?马克思(1867年):在工厂里我们有一套无生命的机制,这种机制是独立于工人之外的,工人仅仅成为它的活的附属物......与此同时,工厂的工作最大限度地耗尽神经系统,它废除了多方面的体力劳动,并且剥夺了无论是身体还是智力活动中的每一点自由。
压模、钻孔、冲压、敲打、液压工具刺耳的声音、实体碰撞产生的振动,还有实体间相互的摩擦。
他花了很长时间才适应这些噪声。
这些噪声本身遭遇实体时又产生新的摩擦。
噪声不断地反射、混响,形成了持续的节奏,因此每一次回声还没结束就被下一个声响打断,没有声音变弱,也没有声音开始。
就算噪声开始变得缓慢或是他离开车间,它的停止也并不会带来一刻安宁,因为那种持续不断的节奏仍然在他的脑袋里面回响,他听不到别的声音,就好像聋了一般。
这里的寂静就是耳聋。
返乡:他变化的速度比自己的国家要快,旁人眼中都是欣羡和忌妒他在自己的省会下了火车。
在他离开的时候,那些新奇而又陌生的景象让他印象深刻。
而现在,他以一种惊讶眼光看着眼前原本习以为常的事物。
他能听懂人们说的每一句话。
如果一个路过的人,一个陌生人,停下来和他说:你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他的第一反应会是很高兴有一个陌生人用自己的语言和他说话。
别人投来的目光显示出一种非常不同的打招呼方式。
车站外的大广场上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名字,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他们的目光中透露出的不是为他感到羞耻,而是欣羡和忌妒。
他变化的速度比自己的国家要快。
国家的经济状况使他做出了离开的决定,而当他回来时,经济状况不但没有发展,反而似乎倒退了。
在那些移民来自的国家中,南斯拉夫是个例外,到目前为止它的经济增长率是最高的。
在1945年到1965年,它的经济增长率更是达到了世界最高。
对于那些现在在外国工作的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人来说,他们宁愿只拿一半的工资在自己的家乡工作,而这个工资水平也只相当于克罗地亚人均工资的一半。
但关键的是,无论工资如何,这样的工作都不存在。
可以预期的是,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国内的工作数量只能够满足三分之一想要从外国回来工作的人。
土耳其的失业人数正在上升。
在1963年针对土耳其移民做的一个抽样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人认为他们回国之后能够很容易地找到工作。
三年之后,只有百分之十三的人这样认为了。
而现在,这样想的人就更少了。
葡萄牙的人均收入是一年350美元。
它的总人口为850万,据估计有160万人在外国工作。
按照他自己的计划,每一年的返乡都是为最终回来所做的准备。
他的经历中没有任何一点曾让他怀疑过握在手中的钱的力量。
他离实现自己的计划越来越近了。
不仅要在经济上自立,在社会地位上也要自立。
拿到做完的工作应得的所有工资。
拥有一家商店。
运营出租车服务。
开一个汽车修理厂。
买下更好的土地,精耕细作。
买一辆拖拉机。
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
有些时候:成为一个裁缝。
在一间办公室中工作。
修理无线电。
买下土地,然后租赁给别人工作。
开展一项摄影的业务。
销售来自城市里的商品。
这些都是他为最终回去之后所做的打算。
他不打算继续在工厂里面工作。
(工厂也没有这样的工作可以给他做。
)他在公交车站附近找到一辆车,开车的是两个从苏黎世来的同胞。
他们要去的地方离他的村庄很近。
其中一个人想要一些钱,他给了。
车开起来后,他们用从城市买来的打火机点燃了香烟。
他们经过第一只动物哨兵,经过自己的朋友。
路旁停着板车,还有拿着小梨子卖的男孩们。
他在车里坐着休息,这辆车是他工作的那座大都会生产的。
他已经成为城市里最新的传言了。
他的身上穿着那里的衣服,他的脚上穿着那里的鞋,他有三只走时精确的手表。
树木静静地站在自己的位置上。
他从传言中回过神来,摇下车窗,看着他的村庄一点点靠近。
在过去的十一个月里,他一直把钱寄回这里。
母亲在他的臂膀中显得那么纤弱而瘦小。
接下来的整整一个月里,他都不需要照片了。
他还活着的叔叔用一种不同的眼光看着他。
很难说这是出于对他获得的成就的尊重,还是因为叔叔离死亡越来越近了。
一年以来,他头一次得到人们的认可。
一年以来,他头一次可以表现出温和有礼。
一年以来,他头一次可以选择沉默。
人们谈论着他最终的归来。
声明:本网站的主要内容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及东西方的民俗文化,并非严谨的科学研究成果。
仅供娱乐参考,请勿盲目迷信。
本文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如有内容侵犯您的合法权益,请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第一时间安排处理。